2009年3月31日 星期二
《再見天人菊》讀後
少兒小說討論課,討論到李潼《再見天人菊》開始,我發覺學妹們似乎頗喜歡討論小說和現實間的差異。就單《再見天人菊》而言,事實上之前還真有許多研究著重於小說與澎湖景緻、地理、人文等等的差異。
然而,我在讀《再見天人菊》時,卻不是這麼個讀法。或許是因從未到過澎湖吧,書報媒體上所得的訊息也不多,於是便更容易接受小說對澎湖的種種書寫。這是我讀李潼的第二本小說,第一本是《見晴山》,不是很喜歡,總覺得有股瓊瑤味!但讀到《再見天人菊》時,我對李潼的看法便完全改觀,畢竟寫作是漫長的耕耘,長時間的寫作和大量的作品,必然能呈現不同的風貌和成就,不能以偏蓋全。《再見天人菊》中的角色、情感,在在都令我有感同身受的感動!它不以情節取勝,一場二十年後的同學會,也沒什麼情節可寫。但李潼將那群孩子的成長歷程和生活環境寫得真實,遂使小說有了生命,也因此真實而扣人心弦。至於小說中的陶土是否出於澎湖,敘寫是否吻合一方風土,一點無關緊要。就如蘇軾未真到赤壁而都能有傳唱千古的赤壁之作,同屬文學領域的小說又有何不可呢?
讀完《再見天人菊》,令我更想一覽澎湖風物,不是為了比較其與小說的異同,而是為再次體驗讀小說時那份真切的感受。如同民歌手潘安邦唱的「外婆的澎湖灣」,即便耳熟能詳的歌詞都非真眼所見,只因一句「外婆的」便覺得親切,誰管「外婆」是否真住在澎湖灣!
2009年3月30日 星期一
小婉心,大中國
 因為日本兒童文學的課輪我報告宮澤賢治,過晚準備了,真有些吃不消。所以,少兒小說課指定討論的二本小說,直到上課前一天才開始閱讀。四點鐘下課後,我帶著《小婉心》,到貴族世家吃牛排,拿起書來邊吃邊看還邊睡!這書大概和那塊平價牛排一般,愈嚼愈沒滋味!或許是太累了,晚上偷回懶不去上日文,直接回丈人家。每回,丈人總會邀我泡茶。但這天我以隔日的功課未完成推辭了。上了樓,洗完澡,再拿起讀了一半的《小婉心》,躺在床上閱讀,還沒翻讀一頁,又睡著!亮了一夜的燈直睡到天亮!
因為日本兒童文學的課輪我報告宮澤賢治,過晚準備了,真有些吃不消。所以,少兒小說課指定討論的二本小說,直到上課前一天才開始閱讀。四點鐘下課後,我帶著《小婉心》,到貴族世家吃牛排,拿起書來邊吃邊看還邊睡!這書大概和那塊平價牛排一般,愈嚼愈沒滋味!或許是太累了,晚上偷回懶不去上日文,直接回丈人家。每回,丈人總會邀我泡茶。但這天我以隔日的功課未完成推辭了。上了樓,洗完澡,再拿起讀了一半的《小婉心》,躺在床上閱讀,還沒翻讀一頁,又睡著!亮了一夜的燈直睡到天亮!臨上課前二小時,書終究還是看完了,但我還沒時間整理思緒。同學的報告用了「小婉心,小心眼」的題目,我只得按同學的報告取巧的反其所是,也算是一種課堂討論、思辯的練習吧!
首先,我以為作為「歷史小說」,《小婉心》一書的歷史成份實在太稀薄了。它是在一個歷史框架裡的寫作,但所寫的內容,不僅沒有歷史的縮影,反而和時代脫節。小婉心的故事,不過是在那個時代中與世隔絕不知民間疾苦的軍閥家族故事罷了。不過,若以「兒童文學」著重於「兒童」的書寫上衡之,小婉心從尋親的過程中認同自我,還是有其精采之處。
其次,我不懂為何這書被選為「台灣兒童文學一百」。作者人雖於1991年時在台灣寫作,但故事中的時間由民國二O年的「九一八事變」到民國三十八年的「撤退來台」。小說終章才提及「台灣」,寫道:「『不知道台灣是什麼樣子?』船上有人在問。」這樣的小說能算作「台灣文學」嗎?
於是我不禁疑惑,「台灣兒童文學一百」的所謂「台灣」,是指「中華民國」嗎?若是政治上的指稱,那麼或可以說得通,不論中華民國的現況如何,仍然有作家願為其作文留史。但話說回來,當時何不乾脆就叫「中華民國兒童文學一百」?
我當然希望「台灣兒童文學一百」的所謂「台灣」,是政治上也是文化上的台灣。政治上的台灣以其海洋島國的移民特性廣納多元文化,西班牙、荷蘭、原住民、閩客文化…等等,當然也包括流亡、離異的中國。若以此視之,那麼《小婉心》所寫的正是那群離異族群的亡國哀思!自然也是「台灣文學」的一部份。
然而,或許是受到近日來新聞報導上所謂「高級的人種」說的紛擾,課堂上我還是不免意氣地指陳,若放在台灣文學史的發展上來看,我們是否也可以說類似《小婉心》這樣的作品,應屬於台灣的「貴族文學」或「高級文學」吧!
2009年3月25日 星期三
我的風箏我的夢

1.
買一架風箏,繫好線,起風時往天上一揚,轉動著線軸,它自然而然地就飛上了天。就這麼簡單,拉著線便也拉著風箏,還些許無聊呢。但我不知怎地就是喜歡!對一向喜愛繁雜而輕視簡單的我而言,這真是有些奇怪的!
2.
印象中我還記得我的第一架風箏,是爺爺糊給我的。骨架用的是編竹籃剩下的竹子,爺爺用柴刀將竹片修得更細長,取了二支,將其中一支折彎,用肥料袋的縫繩當弦固定弧度,直的一根當龍骨交叉,再糊上日曆紙,便完成了。我興奮地,在街道上,從街頭奔到街尾,風箏自然也從街頭飛到街尾,雖然只飛了屋簷的高。
3.
原來風箏可以飛得又高又遠,這是我上國中自己能動手做風箏後,才知道的事。我也不用街頭街尾地奔跑了,就站在自家的樓頂,拿了兩綑母親的車仔線,起風時往天上一揚,自然順勢起飛,一綑用盡時,小心地拉住線頭,再接上一綑。這一飛可以飛過田埂、河渠,飛向集集大山。那裡,爺爺也一定看到了我的風箏,看到我已成長。
4.
會不會風箏也是另一個想飛的夢?來台東求學我還帶來風箏,課餘便一個人到海邊施放。這麼好的風,不曉得為何大家都不放風箏?天上就這麼一只,好不孤獨!現在的孩子不放風箏嗎?現在的孩子不做夢嗎?班花說自從我把風箏帶來台東,台東就不起風!不起風也有不起風的放法,東風不來,可以等待!
5.
我喜愛放風箏,雖然只是簡單無聊地拉著一條細線,一條細線牽繫著我童年的夢!
買一架風箏,繫好線,起風時往天上一揚,轉動著線軸,它自然而然地就飛上了天。就這麼簡單,拉著線便也拉著風箏,還些許無聊呢。但我不知怎地就是喜歡!對一向喜愛繁雜而輕視簡單的我而言,這真是有些奇怪的!
2.
印象中我還記得我的第一架風箏,是爺爺糊給我的。骨架用的是編竹籃剩下的竹子,爺爺用柴刀將竹片修得更細長,取了二支,將其中一支折彎,用肥料袋的縫繩當弦固定弧度,直的一根當龍骨交叉,再糊上日曆紙,便完成了。我興奮地,在街道上,從街頭奔到街尾,風箏自然也從街頭飛到街尾,雖然只飛了屋簷的高。
3.
原來風箏可以飛得又高又遠,這是我上國中自己能動手做風箏後,才知道的事。我也不用街頭街尾地奔跑了,就站在自家的樓頂,拿了兩綑母親的車仔線,起風時往天上一揚,自然順勢起飛,一綑用盡時,小心地拉住線頭,再接上一綑。這一飛可以飛過田埂、河渠,飛向集集大山。那裡,爺爺也一定看到了我的風箏,看到我已成長。
4.
會不會風箏也是另一個想飛的夢?來台東求學我還帶來風箏,課餘便一個人到海邊施放。這麼好的風,不曉得為何大家都不放風箏?天上就這麼一只,好不孤獨!現在的孩子不放風箏嗎?現在的孩子不做夢嗎?班花說自從我把風箏帶來台東,台東就不起風!不起風也有不起風的放法,東風不來,可以等待!
5.
我喜愛放風箏,雖然只是簡單無聊地拉著一條細線,一條細線牽繫著我童年的夢!
2009年3月18日 星期三
《落鼻祖師》和《情書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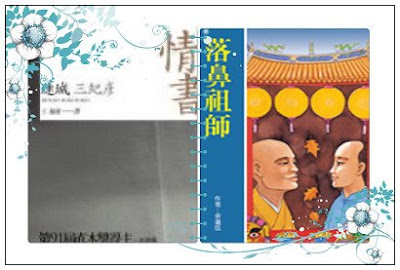
上週的少兒小說課討論《落鼻祖師》。說實在我實在不怎麼喜歡這本小說,甚至嫌它寫得像八點檔,這樣的批評或許有失公允,不中聽,但它的確是我內心個人喜惡的真實感受。
我從不認為寫給孩子看的作品,該迴避某些敏感性的問題,諸如愛情、犯罪、死亡、乃至於性愛。小說本來就是以人生的經驗為藍本,無可避免也必當盡力的去處理這些問題。然而,小說不是連戲劇,更不是社會新聞版。小說既為文學作品,必該有文學作品的規範。這是我對小說的一點看法,以之衡量《落鼻祖師》,我不喜歡它在愛情的描刻上,太過露骨,如時下的八點檔連續劇一般。有人將書中的兩家水火間的男女情愛,比為「羅密歐與茱麗葉」,失之千里!
讀這本小說時,我同時在讀連城三紀彥的《情書》。後者,書中收錄了五則短篇,全都寫男女情愛。說穿了寫的不過是「愛上不該愛的人」而已。但在書中,我們看到了原來這麼庸俗的人間情愛,可以變化各種不同的寫法,不!嚴格地來說,其實,連城三紀彥的寫法也只有一種,或者說,雖各有不同的鋪陳架構,但共同的特色是-「含蓄」。不知是否日本人表達情感的方式使然,抑或是作者本擅長推理類型的寫作。這種「含蓄」的寫作,不同於一般推理書中的矇蔽讀者,吊讀者胃口。反倒比較像是一步步的逼進讀者的底限。讀者在閱讀的同時,答案其實都已呼之欲出,作者的寫作只是不斷的刺激讀者掀開底牌。讀者的你,能容忍這般的情愛嗎?你是否也偷偷跨躍過道德的鴻溝?無論是現實的,還是心中的!
也因此,讀《情書》造成一種心中的「拉扯」,這是小說之所以憾動我的力量,而這股力量來自於「含蓄」,蓄而未發乃能持久!
《落鼻祖師》雖是兒童小說,也觸及了人間的情愛,但我不認為給孩子閱讀的作品在表達上就該「簡單」,因為簡單往往流於草率;在人間的情愛處理上,更不該「露骨」,露骨容易變得肉痲!
2009年3月14日 星期六
戀戀北迴線
講來見笑
昨昏讀報紙拄知影,有人寫了一首名叫「戀戀北迴線」的歌,真符合我目前每禮拜坐火車去台東讀冊的心境。就按呢,我由YOUTOBE搜尋,拄知原來這首歌之所以受到重視,是因為舊年陳雲林來台灣時,中華民國警察暴力侵入唱片行禁播事件。YOUTOBE頂頭嘛有新聞影片。時過數月,拄知影有這件代誌,看著新聞影片,猶原使人義憤填膺。本來想欲聆賞「戀戀北迴線」親切優美的歌詞、旋律的心情,瞬間全化為憤慨!彼个美麗的後花園,彼个青山綠水,竟然被如此的屯踏!
哀哉!咱的台灣!咱的母親!
2009年3月13日 星期五
2009年3月11日 星期三
寂寞˙看花

張愛玲又有遺作出版了,在花姐的網誌上有詳細的討論。
晚上在餐館吃飯時看到聯合報上刊載的一篇文章:<出軌我也有過 我沒有胡蘭成的誠懇>,正好驗了下午文學理論課上一段雷蒙威廉斯<文化與社會>裡引用卡萊爾的話:
我們稱讚一件作品,不是說它「真」,而是說它「強」,我們的最高讚美是說它「感染」我們。
我們的「比較優越的道德」應該說是「比較低的犯罪力」才恰當,它不是出於對美德的大愛,而是出於警察的完美工作:出於那位更精細,更強大的警察-輿論。(<文化與社會>P62)
於是,這個世界,
這們我原本所鍾愛的文學世界,
在面對這樣的"強"勢下,
在服膺輿論的壓迫下,
「真」和「美德」便被染上了寂寞的顏色!
也唯有來此看花,那顏色才一時明白起來!
Ps.感謝有花領我們看花!走出這些天來寂寞的心情。
2009年3月9日 星期一
《魯冰花》討論心得筆記

(圖片擷取自電影魯冰花)
1. 天狗食月
古茶妹浮起腰身瞥了一眼弟弟的畫:哎呀,糟透了!茶妹差點兒就要失聲驚叫出來。看,整張圖紙都塗滿了灰黑的顏色,一點兒也看不出到底是畫些什麼。他總是這個樣子,連天空他也要那個樣子塗下去,而且有時要塗上紫色,有時卻又一片黃色。哪有這樣的天空啊,茶妹不禁弟弟捏了一把冷汗。
……
(郭雲天):「各位小朋友,請大家仔細看看。大家都看不懂這張畫到底畫的是些什麼,是嗎?古阿明小朋友剛才說他畫的是天狗吃月,大家一定會以為那不像狗,那圓圓的也不像月亮,對不對?好,畫畫並不一定要像,這就是說不一定要人家看懂。一張畫的好壞,雖然有好多條件,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色調。…好了,我們想到月亮要慢慢兒暗下來,就覺得很可怕,這張畫可以使人起一種可怕的感覺,這是因古阿明畫得太好的緣故。古阿明小朋友真是了不起。…」
2. 老鼠和小貓
郭雲天取出了那副老鼠和小貓。
「呀!」林雪芬瞪眼說:「真是異想天開。」
「不瞞你說,我是越發覺得這位小朋友了不得了。像這種有點卡通意味的表現,顯出了一股力量。這裡頭有自我,有強烈的主張。我幾乎要認為這才是兒童繪畫的最高目標呢。還有這種顏色的配合,我真願意說這就是馬蒂斯的作風。」
「真有那麼了不起嗎?我倒是有些弄糊塗了。」
雪芬把畫接過來細看。郭雲天移了幾步走到雪芬背後,從她的肩上看那張畫。
「兒童們喜歡把印象最深刻的東西誇大表現出來。我猜古阿明一定很痛恨這隻大老鼠。這隻小貓可能就是他的英雄思想的流露。小朋友們大多有豐富的英雄思想的。」
「這角落的呢?」
「這個嗎?我也不太明白。像是一種小動物,不過他的用意怎樣,我也莫名其妙。」
3. 水牛與牧童
郭雲天彷彿已看到古阿明被愚庸的環境壓迫下來,永生埋沒草萊-成了個貧窮的農夫,永久不能發揮才能。……
……
他匆忙地把那些畫收拾好。恰巧最上面的一幅是古阿明的畫。那是一頭水牛,犄角奇大,幾乎佔滿了整個畫面的三分之一。左下角是一個牽牛的牧童。看來這牧童小得還沒有一隻牛角大。但也因此顯出了那隻牛角的強大有力。這些雖然那麼不均衡,可是任誰都可看出作者的主張如何,意圖在哪裡。而那種由原色構成的鮮豔色彩,更具有一股叩人心絃的力量。
「這是馬蒂斯的手法啊…」
郭雲天低低地自語著。於是,他又沈思了。我真的救不了這樣天才的幼苗嗎?
4. 茶蟲
古阿明畫的是茶蟲。那真是個奇異的幻想世界。在一面圖案化的綠色畫面上,各種各樣的大小茶蟲畫得猙獰可怖。此外還有幾個人物-古阿明曾向郭雲天說那三個人是姐姐,小弟弟和他自己。茶蟲有的在拼命地啃茶葉,有的在吃畫面上的一個人物手裡捧著的飯,有的在吃另一個人物的衣服。古阿明那小小的心靈裡的憤恨與恐懼,靠著他那獨特的,大膽的筆觸,毫無遺漏地表露出來。
5. 未畫出的畫
好多天來,古阿明都在盼望著這個禮拜六和禮拜天。他決定要用水彩來畫割稻的景色。他很多天來就在腦海裡描繪那一幅金黃色的燦爛收割圖-一片稻穗、夕陽、枯黃的稻葉和黃色的稻束。還有,割稻人的竹笠,他們那被泥巴沾污的衣褲,他們那健康的膚色。簡直是一片黃色世界。他幾乎是三步拼做兩步飛奔回家的。
古茶妹浮起腰身瞥了一眼弟弟的畫:哎呀,糟透了!茶妹差點兒就要失聲驚叫出來。看,整張圖紙都塗滿了灰黑的顏色,一點兒也看不出到底是畫些什麼。他總是這個樣子,連天空他也要那個樣子塗下去,而且有時要塗上紫色,有時卻又一片黃色。哪有這樣的天空啊,茶妹不禁弟弟捏了一把冷汗。
……
(郭雲天):「各位小朋友,請大家仔細看看。大家都看不懂這張畫到底畫的是些什麼,是嗎?古阿明小朋友剛才說他畫的是天狗吃月,大家一定會以為那不像狗,那圓圓的也不像月亮,對不對?好,畫畫並不一定要像,這就是說不一定要人家看懂。一張畫的好壞,雖然有好多條件,但今天我要跟大家談談色調。…好了,我們想到月亮要慢慢兒暗下來,就覺得很可怕,這張畫可以使人起一種可怕的感覺,這是因古阿明畫得太好的緣故。古阿明小朋友真是了不起。…」
2. 老鼠和小貓
郭雲天取出了那副老鼠和小貓。
「呀!」林雪芬瞪眼說:「真是異想天開。」
「不瞞你說,我是越發覺得這位小朋友了不得了。像這種有點卡通意味的表現,顯出了一股力量。這裡頭有自我,有強烈的主張。我幾乎要認為這才是兒童繪畫的最高目標呢。還有這種顏色的配合,我真願意說這就是馬蒂斯的作風。」
「真有那麼了不起嗎?我倒是有些弄糊塗了。」
雪芬把畫接過來細看。郭雲天移了幾步走到雪芬背後,從她的肩上看那張畫。
「兒童們喜歡把印象最深刻的東西誇大表現出來。我猜古阿明一定很痛恨這隻大老鼠。這隻小貓可能就是他的英雄思想的流露。小朋友們大多有豐富的英雄思想的。」
「這角落的呢?」
「這個嗎?我也不太明白。像是一種小動物,不過他的用意怎樣,我也莫名其妙。」
3. 水牛與牧童
郭雲天彷彿已看到古阿明被愚庸的環境壓迫下來,永生埋沒草萊-成了個貧窮的農夫,永久不能發揮才能。……
……
他匆忙地把那些畫收拾好。恰巧最上面的一幅是古阿明的畫。那是一頭水牛,犄角奇大,幾乎佔滿了整個畫面的三分之一。左下角是一個牽牛的牧童。看來這牧童小得還沒有一隻牛角大。但也因此顯出了那隻牛角的強大有力。這些雖然那麼不均衡,可是任誰都可看出作者的主張如何,意圖在哪裡。而那種由原色構成的鮮豔色彩,更具有一股叩人心絃的力量。
「這是馬蒂斯的手法啊…」
郭雲天低低地自語著。於是,他又沈思了。我真的救不了這樣天才的幼苗嗎?
4. 茶蟲
古阿明畫的是茶蟲。那真是個奇異的幻想世界。在一面圖案化的綠色畫面上,各種各樣的大小茶蟲畫得猙獰可怖。此外還有幾個人物-古阿明曾向郭雲天說那三個人是姐姐,小弟弟和他自己。茶蟲有的在拼命地啃茶葉,有的在吃畫面上的一個人物手裡捧著的飯,有的在吃另一個人物的衣服。古阿明那小小的心靈裡的憤恨與恐懼,靠著他那獨特的,大膽的筆觸,毫無遺漏地表露出來。
5. 未畫出的畫
好多天來,古阿明都在盼望著這個禮拜六和禮拜天。他決定要用水彩來畫割稻的景色。他很多天來就在腦海裡描繪那一幅金黃色的燦爛收割圖-一片稻穗、夕陽、枯黃的稻葉和黃色的稻束。還有,割稻人的竹笠,他們那被泥巴沾污的衣褲,他們那健康的膚色。簡直是一片黃色世界。他幾乎是三步拼做兩步飛奔回家的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週的少兒小說討論《魯冰花》,老師提點了小說中的許多「對比」,包括貧與富、兒童與成人、男性與女性、古阿明與林志鴻…等等。除了「對比」之外,我個人看到比較多的是「對立」,這「對立」從這五幅被視為小說意象的圖畫中呈顯出來。天狗與月、老鼠和小貓、水牛與牧童、茶蟲與茶園,無一不是對立。最後的未竟之畫,更是理想與現實的對立。我在想:
1. 同時在寫大河小說的鍾肇政,寫了這麼個「小品」的用意?
2. 那些大河小說真如論者所認為,只是單純的「為受難的先民史詩」而已嗎?1960年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已15年了呀!這些歷史的書寫難道不是現代史的書寫嗎?為再次被殖民中的台灣子民書寫!
3. 論者以為鍾肇政「缺乏鮮明的旗幟」,但在那個白色恐怖、言論不自由的年代,不標舉旗幟或許才是最明哲的做法吧!像畫裡的「小貓」,任由「碩鼠」欺凌,但古阿明仍寄望於「小貓」長大!
4. 從「天狗食月」到「未畫出的畫」,不正是象徵一個變異不安的時代,向和平安康的世界有所期待嗎?
5. 不標舉旗幟的鍾氏小說,因此而可久可大!像是古阿明的畫,不能為愚庸的社會改變什麼,但在畫中定然記錄了什麼!
上週的少兒小說討論《魯冰花》,老師提點了小說中的許多「對比」,包括貧與富、兒童與成人、男性與女性、古阿明與林志鴻…等等。除了「對比」之外,我個人看到比較多的是「對立」,這「對立」從這五幅被視為小說意象的圖畫中呈顯出來。天狗與月、老鼠和小貓、水牛與牧童、茶蟲與茶園,無一不是對立。最後的未竟之畫,更是理想與現實的對立。我在想:
1. 同時在寫大河小說的鍾肇政,寫了這麼個「小品」的用意?
2. 那些大河小說真如論者所認為,只是單純的「為受難的先民史詩」而已嗎?1960年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已15年了呀!這些歷史的書寫難道不是現代史的書寫嗎?為再次被殖民中的台灣子民書寫!
3. 論者以為鍾肇政「缺乏鮮明的旗幟」,但在那個白色恐怖、言論不自由的年代,不標舉旗幟或許才是最明哲的做法吧!像畫裡的「小貓」,任由「碩鼠」欺凌,但古阿明仍寄望於「小貓」長大!
4. 從「天狗食月」到「未畫出的畫」,不正是象徵一個變異不安的時代,向和平安康的世界有所期待嗎?
5. 不標舉旗幟的鍾氏小說,因此而可久可大!像是古阿明的畫,不能為愚庸的社會改變什麼,但在畫中定然記錄了什麼!
2009年3月7日 星期六
夜讀
2009年3月5日 星期四
波妞的碗公

上週六孩子的學校舉行家長日,所以學校在星期一補假一天。那個人乾脆也放一天無薪假,說為帶孩子去吃下午茶,不得已也只好跟了去。人有了年紀,最好還是少暴飲暴食,吃了二回生魚片後,再幾杯涼麵下肚,也就差不多了!孩子拿出塗鴨本來畫畫,我也順便要了一張,照著畫冊畫一張波妞。邊畫的同時,邊向那個人提起人家現在連波妞吃泡麵用的碗都有得買,那個人笑而不答,似乎就是並不反對囉!
上網拍搜了一下,賣家還不止一家,訂價4200日幣,折合台幣只賣1500元應該還算合理。正要下標時,我又有些猶豫了,一個「碗公」要1500元,捧著一個1500元的碗公來吃一包15塊錢的泡麵,會不會太誇張?用這樣的「碗公」來吃泡麵,寫起文章來或許能文思泉湧也說不定!雖然,也給了自己很充份的理由,但還是下不了手,真買回來,也不知如何向那個人報賬,還是算了!
上網拍搜了一下,賣家還不止一家,訂價4200日幣,折合台幣只賣1500元應該還算合理。正要下標時,我又有些猶豫了,一個「碗公」要1500元,捧著一個1500元的碗公來吃一包15塊錢的泡麵,會不會太誇張?用這樣的「碗公」來吃泡麵,寫起文章來或許能文思泉湧也說不定!雖然,也給了自己很充份的理由,但還是下不了手,真買回來,也不知如何向那個人報賬,還是算了!
訂閱:
文章 (Atom)

